- · 文艺理论与批评版面费是[01/26]
- · 《文艺理论与批评》投稿[01/26]
- · 《文艺理论与批评》期刊[01/26]
礼赞大师 | 郭绍虞:披沙拣金,为中国文学批评(3)
作者:网站采编关键词:
摘要:(1937年哈佛燕京学社印行,70年代末补充修订后中华书局重版) ,以及《沧浪诗话校释》《诗品集解》《杜甫戏为六绝句集解》等多部专书研究,著成《
语法、修辞、词汇三者相结合,而汉语之特征显。汉语之特征显,然后吸收外人之学,取其分类之长而活用之,则洋为中用,而不为西语陈规所束缚,同时复使昔人《古书疑义举例》、《经传释词》以及《文则》一类之书成为科学化、通俗化,则古为今用,亦不致抱残而守阙,斯则最根本、最基础之步骤。
三十年代起,郭绍虞开始研究古代文学的语言问题,背景正是新诗句法越来越欧化,遭人诟病,他希望能从旧文学里为白话文学找到药方——他也是一个写新诗的诗人呐!在《中国语词之弹性作用》和《中国语词的声音美》等文章中,他指出中国旧文学富含语词升缩、分合、变化、颠倒等修辞技巧,而新文学作家如能学习文言文的这一长处,便能让白话文作品更富音乐性,声情并美。他从语言形式出发,认为自由化、散文化和语体化是中国文学的演进趋势,由此试图建立新旧文学之间的传续关系,解决文白之争,调和而务实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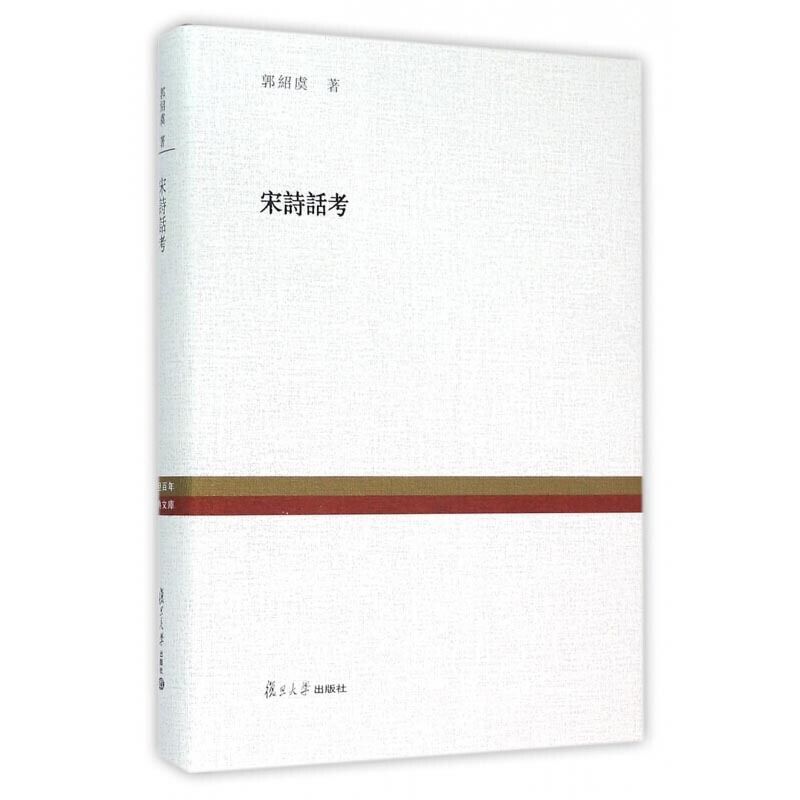
不愿出山也好,便甘下海也好。吾行吾素耳,汝安则为之,谈不到高调低调!
各见平生怀抱,各显本来面貌!“纡辔诚可学,违己讵非迷”,原不关高调低调!
此后,郭绍虞一度在私立中国大学任教。1943年,他匆促南下,将家人安置在苏州,许多衣服用具都弃之不顾,但对自己搜藏得到的清人诗话资料,却不忍割舍。单身一人来到“孤岛”上海后,他为叶圣陶的开明书店编书编杂志,同时在大夏大学等校兼课。曾在大夏念书的儿童文学作家、翻译家任溶溶回忆,郭绍虞这时候一个人住在开明书店编辑部三楼,睡在一张帆布行军床上。
??抗战胜利后,他愤怒于蝇营狗苟、无奇不有的社会现实,接连发表《民主与狂狷精神》《论狂狷人生》《论勇与狂狷》等文,号召知识分子不要“中行”,而要“狂狷”,主张特立独行、不说谎话,以肃清汉奸心理:
乡愿之病在于伪,国愿之病在于滑。……呼之为牛可以应之为牛,呼之为马可以应之为马……道家所谓“自然”,佛家所谓“随缘”,都给他们应用到恰好处。……所以自己没有立场,也就变作没有骨气;所以平时无所谓操守,遇变时就无所谓气节。
1946年,同济大学创立文学院中国文学系,郭绍虞任教授兼系主任,同时在多校兼职。他加入了上海大学教授联谊会,即“大教联”,积极投身民主运动。1950年,同济文法学院并入复旦大学,郭绍虞出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,后来还兼任图书馆馆长、古代文学研究室主任、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名誉所长等职,在复旦大学度过了后半生的34年。
??出任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以后,郭绍虞锐意改革。据唐弢回忆,他约请了不少当时在上海的文学家去讲课,其中有冯雪峰、胡风、李健吾、王元化等等。郭绍虞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入党不久,便将他早年用教书薪酬在苏州建的99间房屋全部捐献给国家。在学术研究上,一直立志用科学方法重述旧学的郭绍虞,也努力根据新的理论来修改《中国文学批评史》。最早,他是站在“纯文学观”的立场来看古代文学批评的,依据文学观念的演变将中国文学批评史分为三个时期:演进期、复古期、完成期。1934年,《中国文学批评史》上册完成时,郭绍虞向胡适求序,胡适虽不满意于这三个分期的命名,并提出若干可议之处,但还是写道:“读者的见解也许不一定和郭君完全一致,但无论何人都不能不宝贵这一巨册的文学批评史料……他确能抓住几个大潮流的意义……使人格外明了文学变迁的理论的背景。”序言写成后未用,郭绍虞将序末二段收入自序。书出版后,钱锺书在《大公报·文艺副刊》上作《论复古》一文提出质疑,认为文学领域不存在古今、新旧的冲突,后来者未必比先起者内容结构更高明、价值更好或引起更大美感,历史进化论并不适用于文学;且所谓进化必然包含目标,然而历史演变无穷尽,这一时的顺流逆流将来可能会翻转。郭绍虞再作《谈复古》一文辩驳,他说自己绝不是“为学时髦而敌视复古”,且已在书序中说明:“曰复古,曰完成,都是不甚恰当的名词,亦强为之名而已。……复古的结果,正可以创造一种新文学。”对此,20世纪过去后,叶辉、周兴陆在《复旦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》一书中评述说:“在今天看来,用演进/复古、文/质、形式/内容的对立与转化来概括原本丰富复杂的古代文学批评史,不免失之偏颇、机械,但这种‘二元对立'恰恰是20世纪前期大部分时间里人文学者的最基本的思维模式。这种思维模式是与革旧布新的时代大势相一致的,也体现出人文学者从旧的文化遗产中寻求新动向、新萌芽的努力。”
文章来源:《文艺理论与批评》 网址: http://www.wyllyppzz.cn/zonghexinwen/2021/0902/550.html